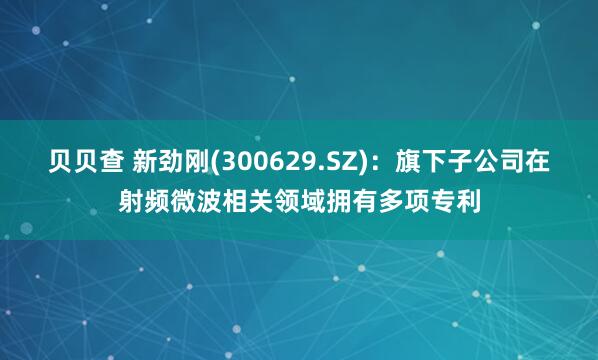章武三年春,白帝城的晨光透过殿宇的窗棂,洒在刘备苍白的脸上。御榻旁,十二岁的刘禅穿着不合身的亲王冕服,双手攥着衣角,指尖泛白。他能闻到空气中浓郁的药味,也能看到父亲眼中强撑的光芒,还有侍立在侧的诸葛亮那身一丝不苟的青色朝服 —— 那是他自记事起,就象征着安稳的颜色。
“阿斗,过来。” 刘备的声音微弱却有力,刘禅踉跄着上前,被父亲枯瘦的手握住。殿外传来江风拍打船帆的声响,像极了去年夷陵战场上士兵的呐喊。他不敢抬头,只听见父亲对诸葛亮说:“君才十倍曹丕,必能安国,终定大事。若嗣子可辅,辅之;如其不才,君可自取。”
这句话后来被《三国志》郑重记载,成为千古君臣相知的典范。但当时的刘禅,只觉得诸葛亮的呼吸顿了顿,随后便是掷地有声的回应:“臣敢竭股肱之力,效忠贞之节,继之以死!” 他偷偷抬眼,看见诸葛亮的眼眶泛红,而父亲的手,在那一刻松了些力气。
展开剩余88%野史《蜀世谱》里曾提过,白帝城托孤前夜,诸葛亮曾单独见刘禅,教他三句应对之语:“父命不可违,相父不可疑,国事不可怠。” 那晚刘禅抱着诸葛亮的腿哭了,说怕自己做不好皇帝,诸葛亮摸了摸他的头,说 “慢慢来,臣在”。这段记载未见于正史,但往后数十年,刘禅的许多举动,似乎都印着这三句话的影子。
刘备驾崩后,刘禅在成都即位,改元建兴。登基大典那日,他站在高台上,看着阶下黑压压的文武百官,突然想起父亲临终前说的 “勿以恶小而为之,勿以善小而不为”。身旁的诸葛亮低声提醒他该下旨了,他才回过神,声音有些发颤地念出早已备好的诏书,诏书中 “尊诸葛亮为相父,政事无巨细,咸决于亮” 的内容,被史官清晰地写入了《三国志・后主传》。
那时的成都,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这位幼主。有老吏私下说 “先主百战得天下,后主恐难守”,也有百姓记得刘禅幼时在长坂坡被赵云救下的往事,叹一句 “吉人自有天相”。刘禅听不到这些议论,他每日清晨到相府请教政事,傍晚在书房批阅诸葛亮送来的奏章,案头总放着父亲留下的《先主遗诏》,上面的字迹被他摸得有些模糊。
第二章 相父的背影与帝王的成长建兴五年,诸葛亮上《出师表》,请求北伐中原。那日朝会,刘禅坐在龙椅上,听相父念着 “亲贤臣,远小人,此先汉所以兴隆也;亲小人,远贤臣,此后汉所以倾颓也”,心中五味杂陈。他知道相父是为了蜀汉,为了父亲的遗愿,但每当看到相父鬓角新增的白发,他总想说 “相父歇歇吧”,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
正史记载,诸葛亮北伐期间,刘禅全力支持,将后方的粮草、兵员调度全权交给诸葛亮推荐的蒋琬、费祎。但野史《汉晋春秋》中曾有一段细节:某次诸葛亮北伐失利,自请贬官三级,刘禅在朝堂上沉默许久,最后说 “相父之功,非一纸贬书可掩,朕准你贬官,却仍以丞相之礼相待”。事后蒋琬私下问刘禅为何如此,刘禅说 “相父要的不是惩罚,是让百官看到国法分明,朕不能让他寒心”。
建兴十二年,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的消息传回成都,刘禅正在批阅奏章,手中的笔 “啪” 地掉在地上。他没有哭,只是愣了许久,直到太监提醒他该上朝了,他才缓缓起身,说 “先封锁消息,召杨仪、姜维回朝”。这段反应在《三国志》中只有 “后主闻亮卒,哭失声” 的简略记载,但野史《三国志平话》里,却添了一个细节:刘禅当晚独自去了诸葛亮的相府,在空荡荡的书房里坐了一夜,桌上摆着诸葛亮常喝的蜀茶,早已凉透。
诸葛亮去世后,刘禅废除了丞相制度,改设尚书台,由蒋琬任大司马,费祎任大将军,分掌军政大权。许多大臣对此不解倍悦网,甚至有人上书说 “废丞相恐违先主遗制”,刘禅却在朝堂上回应:“相父在时,朕倚仗相父;相父不在,朕当为蜀汉主心骨。分设官职,是为防权臣专权,亦为让众卿各展其才。” 这一举措,在正史中被视为刘禅亲政的开端,而野史中则有人评价 “后主此举,颇有乃父制衡之术,非昏庸之辈所能为”。
亲政后的刘禅,并非如后世某些传言那般 “沉迷酒色”。《三国志》记载,他曾多次下旨减免赋税,安抚因北伐而疲惫的百姓;还曾亲自到都江堰视察水利,督促官员修缮堤坝。有一次,洛阳的曹魏使者来访,看到蜀汉朝堂井然有序,百姓安居乐业,回去后对曹叡说 “刘禅虽年轻,却治国有方,蜀汉不可轻图”。这段记载被裴松之注引在《后主传》后,成为反驳 “刘禅昏庸” 的重要佐证。
第三章 宦官的阴影与朝堂的暗流延熙九年,费祎被魏国降将郭循刺杀,蜀汉朝堂的平衡被打破。此时,一个名叫黄皓的宦官开始走进权力中心。正史中对黄皓的记载多是负面的,称他 “便辟佞慧,后主爱之”,后来更是 “操弄威柄,终至覆国”。但野史《华阳国志》中,却有不同的说法:黄皓最初只是刘禅身边的小太监,因擅长记录刘禅的日常喜好,比如刘禅喜欢的蜀锦纹样、爱吃的青城山茶,才逐渐得到信任。
刘禅对黄皓的信任,并非毫无缘由。亲政初期,蒋琬、费祎等老臣尚在,刘禅虽有决策权,却仍需倚仗老臣的威望。老臣们去世后,朝堂上年轻官员分为两派:一派以姜维为首,主张继续北伐;另一派以谯周为首,主张休养生息。两派争论不休,刘禅夹在中间,颇为为难。黄皓虽无治国之才,却擅长揣摩刘禅的心思,总能在他烦闷时说些宽心话,这让孤独的刘禅渐渐依赖上他。
延熙十六年,姜维上书请求北伐,刘禅犹豫不决。黄皓在旁说:“姜维连年北伐,损耗国力,不如召他回朝,任个闲职。” 这话被谯周听到,立刻上书弹劾黄皓 “干预朝政”。刘禅见状,只得和稀泥,既没同意姜维北伐,也没罢免黄皓,只是私下对谯周说:“黄皓不过是个伺候朕的太监,朕知道分寸,不会让他乱政。” 这段对话见于野史《蜀记》,虽未被正史采纳,但结合刘禅当时的处境,倒也合乎情理 —— 他既不想得罪主战的姜维,也不想违背主和的谯周,只能借黄皓这个 “缓冲” 来平衡朝堂。
但黄皓的野心终究还是膨胀了。景耀元年,姜维再次北伐失利,黄皓趁机联合部分大臣,想罢免姜维,让自己的亲信阎宇接任大将军。刘禅这次没有妥协,他对黄皓说:“姜维虽有过失,却也是蜀汉老将,岂能因一次失利就罢免?” 正史记载,刘禅虽未严惩黄皓,却也 “疏之”,让他暂时退出了朝堂核心。这段史实常常被人忽略,人们只记得后来黄皓再次得势,却忘了刘禅也曾试图约束他。
景耀五年,曹魏司马昭派钟会、邓艾分兵伐蜀。消息传到成都,刘禅召开紧急朝会。姜维主张 “坚守剑阁,以逸待劳”,谯周却主张 “投降曹魏,保全百姓”。朝堂上争论不休,刘禅看着两派大臣,想起了父亲当年在夷陵之战前的固执,又想起了相父诸葛亮北伐时的执着。他沉默了许久,最后问谯周:“降魏之后,蜀汉百姓会如何?” 谯周回答:“曹魏若想安抚天下,必不会加害百姓,陛下若降,可保蜀地无战火。”
野史《汉魏春秋》中记载,那晚刘禅在宫中祭拜刘备的灵位,哭着说:“父亲,儿子不孝,不能守好您的江山。可若再战,蜀地百姓又要遭难,儿子实在不忍。” 第二日,刘禅下旨投降,派谯周前往邓艾军中献降书。这段记载虽带有文学色彩,却也道出了刘禅投降时的复杂心境 —— 他或许不是一个有作为的君主,却也并非完全冷血无情。
第四章 洛阳的酒杯与 “乐不思蜀” 的真相景耀六年,刘禅带着蜀汉大臣来到洛阳,被司马昭封为 “安乐公”。正史《三国志》中记载了那场著名的 “安乐公宴”:司马昭设宴款待刘禅,席间演奏蜀地乐曲,蜀汉旧臣皆低头流涕,唯有刘禅 “喜笑自若”。司马昭问他 “颇思蜀否?”,刘禅回答 “此间乐,不思蜀”。
这段 “乐不思蜀” 的典故,让刘禅成为了千古笑柄,被贴上了 “昏庸无能” 的标签。但野史《三国志集解》中,却引了一段未见于正史的对话:宴会结束后,郤正私下对刘禅说 “陛下若再被问思蜀,可答‘先人坟墓在蜀,无日不思’,司马昭必能放陛下回蜀”。后来司马昭果然再问,刘禅照郤正的话回答,司马昭笑着说 “此乃郤正之言也”,刘禅惊讶地说 “诚如尊命”。
这段野史记载,有人认为是刘禅昏庸的佐证,也有人认为是刘禅的 “韬光养晦”。若结合当时的处境来看,刘禅的 “乐不思蜀” 或许是无奈之举。蜀汉刚灭,司马昭对刘禅充满猜忌,若刘禅表现出丝毫思蜀之情,不仅自己性命难保,跟随他的蜀汉旧臣也会遭殃。正如后世学者王夫之在《读通鉴论》中所说:“刘禅之降,非怯懦也,乃保蜀地百姓与旧臣之良策也;其‘乐不思蜀’,非麻木也,乃避祸之智也。”
在洛阳的日子里,刘禅过得并不如意。正史记载他 “食邑万户,赐绢万匹”,看似富贵,实则被软禁在府中,一举一动都有人监视。野史《洛阳伽蓝记》中曾提到,刘禅的府第外常有卫兵巡逻,他想出去散步,都要事先报备。有一次,蜀汉旧臣姜维试图复国,事败被杀,司马昭召刘禅问话,刘禅吓得浑身发抖,司马昭看着他,说 “朕知你不知情,你安心待着便是”。经此一事,刘禅更加谨慎,每日只是饮酒、赏花,从不谈论国事。
泰始七年,刘禅在洛阳病逝,享年六十五岁。司马昭追封他为 “思公”,这个谥号颇有深意 ——“思” 既有 “追思故国” 之意,也有 “反思己过” 之意。刘禅的葬礼很简单,只有少数蜀汉旧臣前来吊唁,其中就有郤正。野史记载,郤正在刘禅的灵前哭着说 “陛下一生,忍辱负重,世人皆笑陛下昏庸,却不知陛下心中苦”。
第五章 千秋评说:正史与野史中的刘禅刘禅去世后,关于他的评价历来争议不断。正史中,陈寿在《三国志》中评价他 “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,惑阉竖则为昬暗之后”,既肯定了他在诸葛亮辅佐下的政绩,也批评了他后期宠信黄皓的过失。这种评价较为客观,成为后世正史对刘禅的主流看法。
野史对刘禅的评价则更为多样。有人认为他是 “千古昏君”,比如《三国演义》中,罗贯中通过描写刘禅 “乐不思蜀”、宠信黄皓等情节,将他塑造成一个昏庸无能、断送蜀汉江山的君主形象。这种形象深入人心,让许多人对刘禅的印象停留在 “扶不起的阿斗” 上。
但也有野史和后世学者为刘禅鸣不平。比如南宋学者叶适在《习学记言》中说:“刘禅在位四十一年,诸葛亮辅政十二年,其后二十九年,刘禅亲政,若真昏庸,蜀汉岂能支撑如此之久?”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《读通鉴论》中更是直言:“刘禅之智,过于孙皓、陈叔宝多矣。孙皓暴虐,陈叔宝荒淫,皆亡国之君;刘禅则能保全百姓与旧臣,非智不能为也。”
近代学者陈寅恪也对刘禅有独到的评价,他认为刘禅 “降魏之举,乃权衡利弊后的理性选择,而非怯懦。蜀汉国力远弱于曹魏,长期战争只会让百姓遭殃,刘禅投降,实乃仁君之举”。这些评价,结合正史中刘禅亲政后的举措,如减免赋税、平衡朝堂、约束黄皓(虽未彻底成功)等,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位被误解了千年的君主。
正史与野史的记载,后人的不同评价,共同构成了刘禅复杂的形象。他不是完美的君主,有过过失,有过妥协,但也并非完全昏庸无能。他在位四十一年,见证了蜀汉的兴盛与衰落,在乱世中,他或许没有父亲刘备的雄才大略,没有诸葛亮的智谋超群,但他用自己的方式,守护了蜀汉百姓数十年的安稳,也保全了许多蜀汉旧臣的性命。
如今,成都的武侯祠里倍悦网,刘禅的塑像早已不在,但在白帝城、在洛阳的安乐公府遗址,仍有人在谈论这位蜀汉后主。有人笑他 “乐不思蜀”,有人叹他 “忍辱负重”,而刘禅自己,或许早已在历史的尘埃中,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答案 —— 他不是 “扶不起的阿斗”,只是一个生在乱世,想要守护一方安宁的君主而已。
发布于:山西省宜人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